铁屋中的新呐喊:AI时代的狂人日记
近来翻看报章,满眼皆是“AI”二字,仿佛旧时茶馆里众声喧哗的谈资,只不过这回换了些新式名词。
近来翻看报章,满眼皆是“AI”二字,仿佛旧时茶馆里众声喧哗的谈资,只不过这回换了些新式名词。谷歌推出了能对话的搜索,微软给浏览器装上了“副驾驶”,连好莱坞的导演们也争相与算法共舞。这光景,倒让我想起清末洋务派的“师夷长技”——只是不知这回,我们是要“师”出个怎样的天地?
一、窃火者与盗书贼
有朋友从硅谷来信,说OpenAI与博通签了十吉瓦的芯片合约,耗电量抵得上一座城。这使我想起幼时乡间富户通宵达旦的灯火,只不过如今燃烧的不是煤油,而是人类的集体智慧。更耐人寻味的是,那些训练AI的“食粮”,恰是攫取自千万作家的笔墨——正如《华尔街日报》所载, neuroscientists(神经科学家)正在起诉苹果用盗版书籍喂养其“苹果智能”。这岂不是新时代的“窃书不为偷”?
更有一桩公案:Cloudflare的掌门人普林斯,竟学起鉴湖女侠的做派,要给内容创作者筑起“防爬虫”的堤坝。他说AI公司应当像Netflix那样为内容付费,这道理固然不错,但让我想起孔乙己那句“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只不过如今窃文者不再穿着长衫,而是披着代码的华服。
二、赛博格里的礼教
最令人悚然的,是彼得·蒂尔在旧金山的布道。这位硅谷的巨贾,竟将监管AI的法规比作“敌基督”的降临。这使我想起《狂人日记》里那些吃人的礼教,只不过如今的“仁义道德”写在了算法的石碑上。当科技寡头开始用末日预言抵制约束时,恰似旧时乡绅以“祖宗之法”抗拒变法。
更有甚者,谷歌的AI搜索竟对某些政治人物的健康问题三缄其口,而对他人却侃侃而谈。这让我忆起民国时报刊的“开天窗”,只不过如今的空白处,填满了算法的沉默。技术本应是民主的工具,奈何总有人想把它变成权力的权杖?
三、傀儡戏与皮影灯
听闻奥特曼与苹果前设计师艾夫正在研制无屏设备,誓要造出“不像AI女友的计算机朋友”。这让我想起家乡的皮影戏——艺人用竹竿操纵纸人,观众明知是假,却仍为悲欢离合落泪。如今的AI助手,不正是数字时代的皮影戏?只是不知操纵竹竿的,是资本还是权力?
好莱坞的编剧们正在罢工反对AI代笔,恰似当年苏州织工砸毁机器。但历史的吊诡在于,机器终究取代了梭子,而AI或许也将重写创作的规则。问题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我们将把创作的主权交给谁——是交给每个人内心的缪斯,还是少数公司的算法?
四、浮世绘里的众生相
在更广阔的天地里,AI正重塑着人间百态:软银斥资54亿美元押注机器人,仿佛当年晋商投资票号;Meta的智能眼镜在演示中频频死机,像极了《老残游记》里走钢丝的艺人;就连美国总统也分享着AI生成的“神奇医疗床”视频,让人恍惚看到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现代版。
这些光怪陆离的景象,让我想起《点石斋画报》里描绘的西洋奇技。只不过当年的火车轮船尚可见可触,而今的AI却如庄子所言“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我们既渴望它带来便利,又恐惧它吞噬人性,这种矛盾,恰似鲁迅笔下那个既想开窗又怕寒风的屋子。
结语:盗火者的新使命
深夜掩卷,忽见报道称物理学家用传统算法控制核反应堆,拒绝AI的介入。这让我想起《故事新编》里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执着。或许真正的进步,不在于盲目追逐最新潮的技术,而在于找回人类最本真的判断力。
AI时代需要的不是新的“礼教”,而是新的“呐喊”。当算法试图定义人性时,我们更需坚守那些无法被量化的价值:同情、勇气、独立思考。正如鲁迅所言:“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在AI铺就的黄金道上,我们更该走出属于自己的蹊径。
更多推荐
 已为社区贡献9条内容
已为社区贡献9条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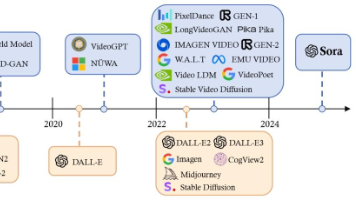





所有评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