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半天堂一半地狱”:人才富集与产业空心化,AI为什么也这么难?
笔者5月份在上海接触到一家专注于AI技术国际供需对接的孵化器,其负责人直言不讳指出国内AI“有人才没场景,有技术没产业”。这与航天产业的处境惊人相似。不禁令人深思:作为工业强国和产业大国,为什么在战略性产业落地上,屡屡显得如此青涩?
笔者5月份在上海接触到一家专注于AI技术国际供需对接的孵化器,其负责人直言不讳指出国内AI“有人才没场景,有技术没产业”。这与航天产业的处境惊人相似。不禁令人深思:作为工业强国和产业大国,为什么在战略性产业落地上,屡屡显得如此青涩?
产业“All in”的战略悖论
▼
前面笔者花了10个多月的时间、用近40万字分析航天产业,搭建了一套与当前主流完全不同的研究框架。在此基础上,延伸出三个关键思考:
1、产业竞争的本质是什么?
比如中美在航天、AI、新能源汽车等高端产业领域的竞争,起决定作用的核心要素是什么?
2、如何判断一个行业是否属于国家战略级行业?
比如太空和低空,哪个更具有战略价值?
3、在战略新兴产业“商业航天”领域存在的问题,在别的行业是否同样存在?
顶层设计、标准体系的缺失,是能力问题还是执行层从根本上不重视?
近期大概翻了翻热度俨然已经盖过太空、并且太空产业化主力部队航天科技等企业也在加大投入的“低空”产业,再结合直接接触和观察到的元宇宙、区块链、AI等行业的一些现象,发现国内产业发展的zc驱动特征非常之显著:一个行业能否聚集关注和热度,zc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zc驱动往往会形成典型的正反馈循环机制:zc出台→白皮书发布→论坛峰会激增→舆论热度攀升→更大zc力度。从系统论视角看,这种自我强化的正反馈系统如果缺乏负反馈调节(如市场真实需求校验、技术可行性评估),当输入端的产业基础逻辑存在缺陷时,整个系统将陷入“zc过热-资源错配-效果不彰”的恶性循环。
所以,笔者一直认为,zc必须遵循产业发展规律——就像化学反应需要特定条件,zc的作用主要在于补齐要素和添加催化剂;产业研究的第一要务,正在于厘清这些底层逻辑。
这个基本规律,对任何行业都适用的,必须把握的,也很容易理解的,笔者认为有几个方面:
-
技术不到家,产业跑不快(技术成熟度决定产业演进节奏)
-
需求有多大,市场才能做多大(需求决定产业规模,基建与应用场景培育必须两手抓)
-
无生态,不商业(生态决定产业存续,产业化落地必须着眼于完整的生态体系)
从这几个方面综合看,目前在“低空”领域的投入,颇有些牛刀宰鸡的意味(《低空物流终局:无人机物流的“大规模市场”可能是个伪命题》);而在决胜未来大航天时代的“太空”领域,到目前连宰鸡刀都没有(标准、机制、生态都不健全)。美欧all in“太空”,我们则选择all in“低空”,这个战略逻辑是什么,是值得追问的。
对于AI来讲,目前制约行业发展的核心瓶颈不在技术而在生态建设上,还有前期数字化转型执行不到位造成的诸如数据标准不一、系统割裂等问题(《在中国,大模型的应用困境》)。数字化转型是迎接“数字时代”的基础动作,这些动作不到位,反映了执行层并没有“all in”的决心。也就是在执行层面,AI和航天一样,都没有获得与其战略定位相匹配的资源倾斜和系统性支持。
新兴产业的多维动因
▼
在特定区域,一个产业出现的原因可以有很多,比如:
-
需求驱动:基本生存需求;升级需求;痛点解决需求
-
技术突破:新技术出现;不同领域技术交叉催生新业态
-
资源禀赋:能源、原材料、文化遗产等资源禀赋的开发利用;人才结构、劳动力成本等资源优势
-
文化变迁:比如宠物从“工具”变成“家庭成员”,国内宠物审美从本土的华夏帝王犬、狸花猫转向五花八门的进口品种,宠物经济应运而生
-
升级替代:比如传统汽车电动化出现的新能源汽车行业;植物肉替代天然的动物肉制品
-
国际分工:全球价值链拆分催生专业化细分行业;国际关系变化导致的产业本土化
-
zc放开:比如美国、加拿大的叶子,合法化以后一夜之间变成规模产业了
但一个全新产业的出现,必然以新技术、关键技术突破为前提:
航天的真正产业化就源于航天工程相关技术的发展成熟——可复用火箭技术带来发射成本的大幅降低,叠加人工智能优化决策流程、3D打印加速部件制造等技术协同效应,重构了航天产业的价值曲线。使得大规模卫星组网、载人航天平民化成为可能,推动太空活动从实验室研究、小规模军事应用加速走向真正的产业化时代。
得益于算力、数据等基础设施的成熟,2022年大模型爆发性发展,不仅通过标准化技术栈重构了AI产业范式,使得开发成本断崖式下降、落地周期从数月缩短至数周,更推动AI技术深度融入生产、制造、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展现出前所未有的产业化应用场景,推动数字时代向全面智能化迈进。
“有技术没产业”的困局解析
▼
一切技术探索的终极目标还是造福人类,而产业化(或者说技术平民化)是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社会、惠及大众的关键环节。一个领域出现“有技术没产业”的情况,可能的原因:
一、技术因素:
-
技术成熟度不足,工程化瓶颈未能突破
-
成本曲线未达到商业化临界点,无法形成规模效应
二、市场因素
-
技术解决的是伪需求,真实需求未得到验证
-
现有解决方案性价比更高
-
市场教育缺失,或用户转换成本壁垒较高
三、生态因素
-
基础设施缺失,配套产业链不完整
-
关键环节受制于人
-
标准体系未建立(包括航天在内,国内很多关键领域的共性问题)
四、制度环境因素
-
zc规制冲突,相关的准入和监管机制滞后
-
资源错配,过度追捧技术噱头而忽视长周期投入
-
产学研脱节
在各方以行业基本规律为准绳的情况下,比较容易力出一孔,以我们当前的经济实力、人才资源,技术、市场、生态的问题都相对容易解决。但在完全zc驱动的正反馈体系下,如果产业基础逻辑存在缺陷(比如以上第四条出现问题),整个体系将难以健全。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华为这类具备顶尖实力的企业,也难免举步维艰。
注意是否zc驱动,与企业性质无关,只与zc方向是否符合产业基本逻辑有关。我们再强调一下这个产业基础逻辑:
-
技术不到家,产业跑不快(技术成熟度决定产业演进节奏)
-
需求有多大,市场才能做多大(需求决定产业规模,基建与应用场景培育必须两手抓)
-
无生态,不商业(生态决定产业存续,产业化落地必须着眼于完整的生态体系)
事实上,“有技术没产业”是美国自“去工业化”战略以来遭遇的一个典型困境:伴随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持续挤压,美国一步步变成一个工程化能力流失、劳动力技能结构失衡、各产业严重依赖国际分工的怪物。马斯克的SpaceX虽然算不上什么“人类之光”,但确实为美国的“再工业化”带来一丝希望。
而国内在以“产业升级+工业化深化”构建自主可控高端制造体系、从而扭转中美竞争格局的大背景下,航天、人工智能等核心战略领域却出现“有技术没产业”的问题,这是相当令人费解的。这一矛盾现象直接暴露出,执行部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存在认知偏差的。这一点,单从对“低空”与“太空”的投入差异就可见一斑。
产业竞争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
随着现代创新从线性向网络化演进:
-
创新主体多元化和协同化,例如开源社区中的开发者、众包平台的普通用户、内容网络的用户等,都成为创新的参与者
-
创新过程并行化和迭代化,通过并行工程和敏捷开发,产品的设计、测试、生产等环节可以同时进行,创新过程也不再是单向的和一次性的
-
创新资源开放化和共享化,技术开源和知识、设备共享成为常态,创新要素的全球流动更加便捷
-
建立在网络基础设施基础上的“硬件+操作系统+应用入口”构成数字产业基础架构。通过数字化转型,数字产业与各垂直行业深度耦合,形成以各产业基础架构为“硬件”载体、各类智能中枢为“操作系统”、数字化改造后的场景为“应用入口”的现代产业生态体系。不同行业之间的合作更加频繁,跨界创新成为常态
现代产业竞争已经从单一行业的技术比拼升级为以国家为单位的综合能力体系竞争。
这个能力体系的核心支柱是三个方面:
一、基础要素
-
创新人才梯队:覆盖基础研究、工程转化、技能工人的完整人才结构
-
产业资本及其配置效率:尤其长期资本供给与金融支持效率
-
核心技术掌控:在材料、工艺、装备等产业基础环节的自主可控能力
-
关键资源保障:例如稀土、锂矿等战略性资源的开采与精炼能力,能源系统的可持续性等
二、产业生态构建能力
-
产业链韧性:上下游协同配套能力与应急替代机制
-
创新网络密度:产学研协同效率与技术转化速度
-
应用场景深度:技术与市场需求的精准匹配程度
-
基础设施完备性:算力、网络、能源等新型基础设施支撑
三、规则主导权
-
标准制定能力:主导国际技术标准与产业规范
-
治理话语权:参与乃至引领全球产业治理体系
-
价值分配权:掌控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
-
生态定义权:构建技术路线与商业模式的示范效应
目前看,航天也好、人工智能也好,我们当前在基础要素尤其人才梯队上是有绝对优势的,但规则话语权拱手让人、生态建设缺乏重视(尤其技术转化和应用场景深化),是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然,究其根本,执行层对战略新兴产业的认知偏差还是关键症结。
如果不点破和根除这个问题,我们会永远在关键领域疲于奔命做“追赶者”。尽管过往我们在大部分领域都做到了“后发先至”,但这一定程度得益于美国“去工业化”的战略失误(就像SpaceX在2018年危机时刻能轻松过关并一骑绝尘,离不开我方的系列错失)。
如今,马斯克的SpaceX和特斯拉已经充分验证了美国政商界“再工业化”的决心和能力,对于航天和人工智能等决定未来国运的关键领域,我们不能心存侥幸。
主要参考资料
本文在网络公开资料研究基础上成文,限于个人认知,可能存在错漏,欢迎帮忙补充指正。
更多推荐
 已为社区贡献6条内容
已为社区贡献6条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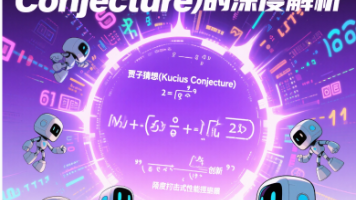





所有评论(0)